我们(即「异见者编辑部」)和劳拉·西塔雷拉的线上采访约定于2025年1月28日,除夕夜当晚。感谢Fluorescent的介绍和石新雨的正式邀约,她们在西塔雷拉出任海南岛电影节竞赛单元评审时与其取得联系,给了我们这次宝贵的机会接触这位身兼多职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电影人。这篇对话并不希望过多谈论具体影片的含义,而是希望借作者的视角,观察这种在集体中创作的形式是如何产生,并如何和更大的电影世界发生联系。
感谢劳拉导演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提议,并抽出时间和我们通过邮件进行了额外补充。采访以西英双语进行,感谢汪米拉作为西班牙语顾问帮助我们完成采访的提问和部分文稿的翻译。最初发表于「异见者TheDissidents」公众号。
采访人 TWY(英语)、汪米拉(西班牙语)
参与采访 铜tt、夏萝、石新雨、唯唯、D-Will
****
异见者:我们可以首先谈谈您的最新作品《缪缪之谜》(El Affaire Miu Miu, 2024)。这部短片的拍摄速度相当快,且创作环境与你其他作品截然不同。
Laura Citarella(LC):这部短片对我们而言并不典型。通常,潘佩罗小组制作或开发项目时,我们是作品的所有者,也需要自行探索为项目筹集资金,或寻找投资方的方式。但《缪缪》的诞生方式不同,我们更像是被雇佣来完成这部影片。这与我们多年来的工作模式差异巨大。这个项目始于Miu Miu品牌与不同女性导演之间的合作,这个项目已持续多年,去年他们选择我作为导演之一,主动联系并邀请我创作点什么。
异见者:这种合作具体是如何展开的?
LC:我唯一的义务是融入Miu Miu当季(冬季)的服装设计,除此之外拥有的完全自由。于是我的想法是要把两个世界交织:一方面是我此前的电影《迷雾中的她》(Trenque Lauquen, 2022)中的宇宙,另一方面则是时尚的世界,我对这个领域并不熟悉。因此我要做的则是把时尚的世界带入特伦克劳肯市(Trenque Lauquen),让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产生化学反应。虽然短片的制作和创意仍源自我们,但其诞生方式与以往作品不同。它并非由内而生,而是来自外部世界。

异见者:您提到这是受委托创作的作品。潘佩罗的影片,不仅是您的这部作品,也包括阿列霍·莫吉兰斯基或马里亚诺·利纳斯的创作的作品,常源自不同形式的委托。但随着拍摄推进,你们会将原始的委托转化为成拥有个人特点的作品。这个特点似乎贯穿了您个人与潘佩罗的创作历程——在展现作品源头的同时保持了一种个人的艺术。
LC:确实如此。我们的许多电影始于他人雇佣或委托。比如阿列霍的《鹦鹉与天鹅湖》(El loro y el cisne, 2013)和《卖火柴的小女孩》(La vendedora de fósforos, 2017),这两部最初都是关于特定内容的纪录片,并非由我们发起,我们只是参与其中。但随着拍摄的过程,虚构就会出现在这个纪录片领域——最终15分钟的短片可能发展为两小时的长片。这是我们典型的创作方式,具体取决于谁被雇佣去执导那部影片。在Miu Miu项目中,被选中的是我。这次合作更明确,毕竟是为品牌工作,与普通的纪录片不同。通常当我们接手项目时,例如阿列霍会和我说:“我发现通过这部影片,我们可以实现这样或那样的可能性”,然后我们便开始思考如何将构思扩展成电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尝试将潘佩罗的微型结构纳入到项目中,这些作品可能始于毫无野心的微小起点,但最终能成为拥有演员阵容和具体野心的影片。
异见者:在《缪缪》中,您融入了《迷雾中的她》的场景与人物,同时将这个意大利品牌的服装与模特编织进影片的谜团中。前作的谜团更多来自具体人物的历史,但在Miu Miu这里,服饰在短片中却如不明生物一般凭空出现,这似乎就扰乱了常见的广告片的秩序。将这种品牌产品融入电影谜题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LC:与品牌合作是奇怪的体验。正如所言,我必须引入这个对我极其陌生的领域——在阿根廷,我们甚至没有Miu Miu门店。我们没有这些因为这是个贫穷的国家,我们没有普拉达或者古驰等品牌门店,我只能在Instagram,或者我前往欧洲或者中国时看到这些。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避免去制作广告宣传,不是为了赞美Miu Miu的服装有多好,而是挖掘它作为虚构,看看它能否成为人物能够去发现的证据。潘佩罗电影创作的核心在于对这种语言,对这种虚构的调查,我们对此有这种执念。因此我选择不改变《迷雾中的她》的宇宙,而是让这个已被构建的世界因时尚的入侵发生变异:当特伦克劳肯的城区,其中的人物以及她们的节奏,开始与这些时尚元素碰撞融合时,会产生一种这种宇宙的奇特图像。对我来说这才是重要的。
同时,我想和同一批人再次合作,虽然人物不同,但演员相同。唯一的例外是埃兹奎尔·皮耶里(Ezequiel Pierri)——他是我的丈夫,他的饰演的”Chicho”是唯一从之前电影中延续的角色。但我喜欢这样像在小剧团一样,其中演员可以扮演不同角色。比如《迷雾中的她》的女主角劳拉·帕德雷斯(Laura Paredes),她在短片中饰演了触发事件的侦探。通过置换角色位置,我们在熟悉的元素中进行实验:只要改变一个元素,整体就发生了变化。这是拓展电影语言和灵感的方式。

异见者:的确,您的电影的迷人之处总是在于,谜题总是在不同人之间被交换和分享。所以我们想更多了解潘佩罗小组的制片方法,以及你们怎么看待自己在阿根廷电影中的位置。作为远在异国的影迷,我们想首先聊聊电影的发行:潘佩罗的一些作品,如《花》(La Flor, 2018)、《迷雾中的她》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放映,并且受到世界影迷的喜爱,《缪缪之谜》则在威尼斯首映后直接上线了YouTube。但另一些作品,如马里亚诺·利纳斯的新作《科西尼:故土乡音》(Popular Tradición de esta Tierra, 2024),虽然在本土获得了热议,但目前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获得过放映。您认为在潘佩罗的作品集群里,是否存在全球与在地的差异?发行是由你们自主掌控还是通过其他渠道?
LC:是的,作为制片公司,我们意识到的最重要的事是每部电影都是独特的,所以不应该套用相同的公式。当然,我们不认为自己是所谓的制片公司,我们总说自己更像是一群影人好友组成的集体,虽然到头来我们也有法律架构,但我们更多时候只是朋友,会花很多时间去聚在一起,因此我们不像一个公司。关键在于理解每一部影片是不同的。我们很惊讶于人们对于《迷雾中的她》的评价,尽管它是独立制作的电影,但我们没有什么营销策略,也没有亚马逊或网飞这种平台的支持。我们自己发行了影片,接着别的发行商还有销售经理等等出现了,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自主管理。
我想最关键的是,一部“小的电影”需要比“大的电影”更多的时间和呵护,当我说“大”的时候,我指的是像《花》或《迷雾中的她》那样的影片,它们更加具备普世的潜力,因此更容易被全世界接受。当然,它们也有各自的身份等等,但总的来说它们更平易近人,我们从观众以及发行和放映等行业人士中也获得了更多反馈。相反,对于有些作品,我们意识到需要用不一样的方式来照顾它们,用更加珍贵的方式。比如,马里亚诺的这部电影,我们认为是一部很杰出的作品,但我们不确定它在阿根廷之外是否能获得同样的反响。这部影片非常具体,讲述的是非常本土的内容,完全不“普世”,尽管我并不认同这点。
另一边,我们有很多很多“小”的电影。比如,我曾拍过一部电影《诗人们去拜访胡安娜·比格诺齐》(Las Poetas visitan a Juana Bignozzi, 2019;和Mercedes Halfon合导),但如果我想要放映它,就很不容易。这部电影对我很重要,和我的关系密切,并且对《迷雾中的她》的诞生也很关键,但我能理解也许是因为语言和翻译问题,也许是因为影片讲的是一位诗人,使得它很难在全世界内被看到。但关键并不是赋予这部电影和《迷雾中的她》相同的发行路线或渠道,因为那不管用。你得找到合适的空间和时机去让电影被看到。
我相信世界应该接受更多这样的东西,但我觉得电影节并不这么想。它们想要更有野心的东西。电影节希望你去制作一次性讲几件事的电影,比如《迷雾中的她》,它是一部虚构作品,并且包含了不同的类型、故事线、演员和场景,并且不断延伸;它和世界、文学和电影的历史都有联系,有很多的对话,因此更容易向世界去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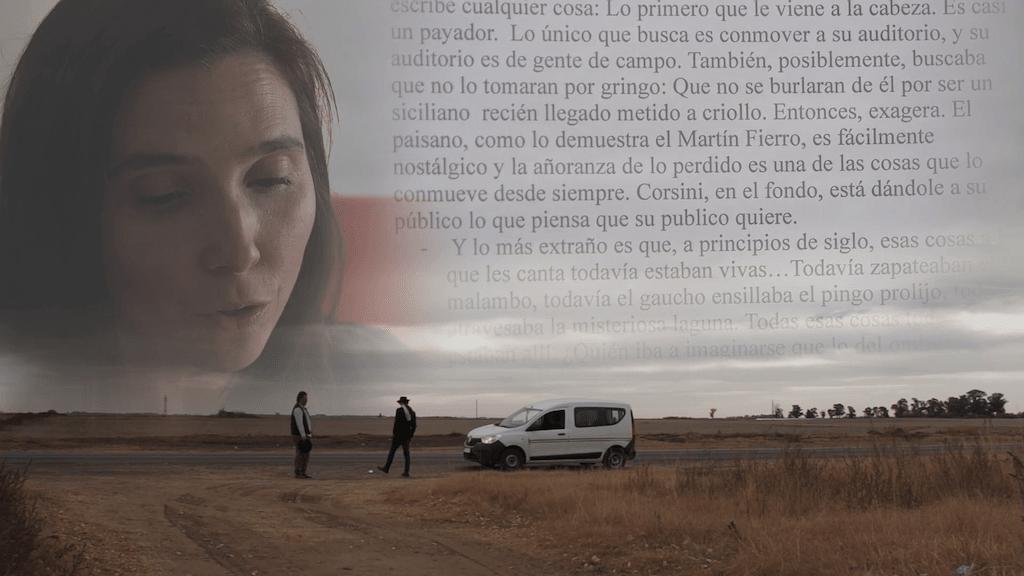

异见者:我们在观看了《迷雾中的她》之后看到了《诗人们》,便立刻意识到这部片子如何催生了《迷雾中的她》的部分叙事内核。这种细节是潘佩罗电影最迷人的特质,电影始终保有具体而独特的时空坐标,作品间也有绵延的关联,似乎一部电影能孕育下一部,同时也折射了国家的变迁。如今阿根廷进入政治新周期,艺术生存环境愈发艰难,这些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挑战如何影响了你们?
LC:我们拥有丰富的创作工具,在过去25年一直以多样的方式制作电影。对潘佩罗而言,身处经济危机、资金短缺乃至从零创造电影,是我们的常态,这方面并无改变。真正发生剧变的是外部环境,当你发现身边的所有人都开始遇到经济或者其它问题,随着物价飞涨;今天的阿根廷政府不仅是右翼政府,不仅停止了对电影以及艺术的支持,还让日常消费变得非常困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成本已高于纽约,生存非常困难,人们经常来不及支付账单。经济危机的现实超越了艺术。整个产业陷入巨大危机,我们看到自己的朋友无法继续工作,生活压力巨大,都感到十分痛苦。更严峻的是,政府不仅停止了对很多同行的扶持,总统米莱及其追随者还对艺术家开始肆意的诋毁,仿佛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错误。他们会举办那种演讲,而我们甚至要向自己的父母解释自己的职业是什么,解释自己在努力工作,不是懒惰的宅家女孩,诸如此类… 他们建构起一套将我们妖魔化的话语体系,在这种暴力言论日常化的国度,维持健康创作的氛围变得异常艰难。当然,我们这些想要继续拍摄电影的人们,仍在寻找突破体制桎梏的方式去创作,不让这些邪恶的人物设计的圈套把我们困住。我们总是通过不同躲避体制的方式去继续拍摄电影,但愈发艰难。
异见者:关于阿根廷的电影体系,我们关注到你们经常谈论INCAA(阿根廷国家电影局)的官僚机制。你们反对INCAA的根源是什么?近年来其政策是否有重大调整?
LC:事实上,我们从未与INCAA合作过,最初是因为其繁琐的官僚程序与我们的创作理念相悖,那种方式对我们来说很荒谬。这么说吧,后来我们试图与阿根廷电影界及INCAA展开对话(尽管对方始终大门紧闭)。我们呼吁制片方式的多元化,希望电影局能接受除了工业化体系以外的其它制片形式,但官方并没有和我们对话的意愿。所以在对牛弹琴的情况下,我们突破了金字塔式工业化制片结构,建立更集体化、水平化的创作模式。我们想和INCAA谈的就是它们没有制片方案的“B计划”,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经常遭遇经济困难的国家里,我们常年要面对这种情况,总是需要有所发明。但INCAA坚持将所有电影的创作套入同一模板:固定的拍摄周期、标准的剧本结构、标配的人员规模。比如说,他们希望你能在六周内拍完一部电影。但以《迷雾中的她》为例,让时间流逝成为影片的一部分:拍摄期间我怀孕了,因此我以孕妇的样子出演了影片;接着,我的女儿出生了,于是她也在电影里出镜。你根本无法向INCAA解释这种创作方式,这些不在它的条例里。
但今天的情况是,米莱以及右翼政权威胁要废除INCAA,我们反而转为支持其存续,因为当下更紧迫的议题是抵抗”电影局不应存在”的荒谬论调。我们决定了当下不是继续发表意见的时刻,我们必须支持INCAA,因为很多你们知道的原因(注:当今大多数阿根廷电影都通过INCAA的资助进行制作)。
异见者:潘佩罗和阿根廷当地的独立机构有什么样的合作,比如MALBA(布宜诺斯艾利斯拉丁美洲艺术博物馆)?
LC:我们既是自己的制片人,也是发行人。唯一的例外是《迷雾中的她》,我们决定与一家非常可靠的国际销售商 Luxbox 合作,因为尽管我一般会负责和发行商或放映商进行交易,但我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要同时兼顾所有角色,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们与影院的合作也是由小组自己管理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发现了对我们有帮助的影院、发行商和代理商,遍布世界各地。我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人际网络,这部分人群能够理解我们为何希望以更激进、更具体的方式发行电影。例如,我们每周发行的影片放映场次从不超过两三场。这样,像我们这样的影片形成的“传闻”(rumor),或被我们称之为“口口相传”(boca en boca)的时间就会更长,影片的生命也会更长久。对于国际发行和电影节而言也是如此。我们自己管理一切,保持沟通。由此一来,电影就不会被独自抛向世界,而是每一步都有人的陪伴——至少在早期是这样。
异见者:是的,我们很赞同这种“陪伴”电影的方式。多年来,潘佩罗也积累了众多合作者,比如英格丽·波克洛佩克(Ingrid Pokropek),她在2023年完成了自己的导演首作《主要音调》(Los tonos mayores, 2023)。潘佩罗是否会主动扶持新导演?未来还有哪些合作者的新作值得期待?
LC:英格丽的作品并非潘佩罗出品。她是与我们共事十年的好友,如今她开启属于自己的创作旅程,是很自然的事,我们也很高兴。但潘佩罗没有参与她的电影。我们仅制作我们四个人的作品:马里亚诺、奥古斯丁(门迪拉哈苏)、阿列霍和劳拉。我们四人发起项目,不接收外部提案。虽然我们经常收到其他人的项目,或者其他人希望和我们合作一些项目,但我们自己手里已经有足够多的在进行了。当然,我们试图和他们保持联系,并在有必要的时候帮助他们。用一句俗话说,我们是一扇“从内打开的门,门内的事情,在我们内心,在彼此之间。”(“Puertas para dentro”, se dice aquí, “de la puerta para dentro, para dentro nuestro, entre nosotros.”)
异见者:潘佩罗的作品在阿根廷的电影文化中处于何种位置?本土评论界如何看待你们的创作?
LC:我不知道。[笑] 近年我们因《迷雾中的她》获得更多关注,参与了不少制片方面的讨论。或许人们终于理解了我们的独立姿态,理解了我们做的事情不是为了最终通向什么别的体制,而是我们25年以来一直选择的生存方式。所以,如今的印象是这么做是有实际的可能性的,是一种严肃的创作方式。这种坚持最初被视为幼稚,但我想如今人们明白了这就是我们想在阿根廷电影界中保持的位置,并且要继续下去。当然,我们想拍一些更大的电影,因为随着我们年岁增长,拥有的时间也更少——我们要养育子女,生活变得复杂。所以,我们如今想拍的电影,会和我们在二三十岁时想拍的有所不同。但即便在Miu Miu的项目中获得了一定的预算,并且我们对预算有坚实的计划,我们希望继续以之前25年的方式去拍摄电影。
异见者:作为潘佩罗几乎所有电影的制片人,您如何统筹各项工作?是否存在特定的方法?
LC:没有固定方法。对我来说很明显的是,制片与导演的职责有着彼此共生的关系:在构思剧本时,我已经在写作的同时完成场景选址、团队搭建等考量。所以写作剧本是制片的一环,因为我有这种双重身份。潘佩罗的创作者都深谙这点:马里亚诺和制片的关系很紧密,并且痴迷于发明不同的生产系统,阿列霍也经常身兼多职。我的特别之处在于,我是官方意义上的”制片人”,我需要能让它推进,获得资金,让一部电影最终落地。它已经是我的生存本能,就像呼吸一样,它就这么一直存在于我的日常中,无论是工作还是休息中。

没有特定的方法,关键是要理解每部电影的本质需求。就像我刚刚说的,《诗人们》是我在拍摄《迷雾中的她》期间拍完的,它们彼此对话。接着我成为了母亲,在那段时间拍摄《诗人们》相对更容易,但是带着满月的宝宝拍《迷雾中的她》就很困难。因此,电影支配生活,生活也支配电影。
重点在于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一部电影需要什么。对于有的电影,你需要的很少。有时候三个人就足够了。马里亚诺最近几年拍摄的电影,包括《故土乡音》,都是他和零星几个人一起拍的,当然我也是制片人,但我甚至不用去拍摄现场,因为他和需要的人在一起,和摄影师、他的车和他的狗狗一起。不需要其他人。当你明白这就是电影所需要的,你就不需要做超出需要的事了。
正因如此,行业本身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有时候这个行业已经习惯了以非常流程化的方式工作,他们觉得必须填满所有的工作表格。但我们不需要这些。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需要服装设计师。例如,在这个场景中,演员可以穿自己的衣服。我们不需要有人来告诉我们要穿什么。所以这是你必须为每部电影、每个场景理解的事情,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异见者:为不同的影片作不同的计划。
LC:是的,并非所有项目都以相同的方式响应结构。每部片的拍摄都会产生相应的新制作结构。
异见者:我们很喜欢劳拉·帕德雷斯和「Piel del Lava」剧团的女演员。能谈谈您与劳拉的合作吗?导演和演员在团队中的关系如何?演员们有什么样的参与?
LC:劳拉·帕德雷斯是马里亚诺·利纳斯的妻子。因此,她除了是我们团队的重要女演员之外,她还嫁给了我们其中一人。因此,这种关系,就像潘佩罗自身一样,也是非常牢固的友谊和感情。这很疯狂,因为这意味着工作和友谊总是融合在一起,并互相影响。她来自「Piel del Lava」组合,她们出演了《花》。她们也可以说是以同样的方式工作的集体,多年来也一直是朋友。在这种友谊中,工作得以实现,而这种工作也建立了友谊,几乎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我认为她非常了解团队合作。关于集体这种东西,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在其中,会很难理解。我觉得劳拉不仅理解,而且也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即作为一个集体如何在这种结构下工作。

异见者:潘佩罗的四位导演似乎也很乐意出现在摄影机前,有时候作为自己,有时候也扮演其它角色。您2023年的短片《特伦克劳肯》(Trenque Lauquen, 2023)展现了您坐在《迷雾中的她》拍摄地的一家电影院外,您的电影正在影院内举行首演,这个等待的场景有种不安的感觉。
LC:我们与表演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同。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在镜头前出现,是因为他/她别无选择,尽管在更多情况下也取决于导演的意愿。另外,与演员朋友和自己的家人共同出演角色,也是一种轻松的方式。但我不知道这是否仅仅与制作问题有关。我认为,这更多地是与在制作其它作品、尝试或实验时所做的决定有关。当我自己必须出镜时,我感觉不是那么自在,至少当我自己担任导演时,我不会选择这么做。我会感到失控,会看不清我本应看到的东西。但正如我前面所说,有时我们别无选择。例如,就《迷雾中的她》中的角色卡门·祖娜(Carmen Zuna)而言,我几乎不可能不亲自出演。
异见者:我们觉得潘佩罗小组是电影和独立剧团的混合体,就像一个持摄影机的小剧团。
LC:是的,很有趣…… 我们在拍《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我们去拍摄时忘了带摄影机。所以有时甚至没有摄影机。[笑] 我们所有人都到了拍摄现场。当我们到了那个地方时,人们问:“摄影机在谁地方?” 然而不,没人带了摄影机。
异见者:[笑] 那是在哪一集?
LC:是在《花》的第三集中。我们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开了两百多公里的车。我当时不在那里。只有马里亚诺、我们的剧组以及两名演员。这件事真的很好笑。但对我来说,这就像在剧场。你知道他们是如何运作的…… 但剧团和电影剧组之间也有区别,通常当你学习制作电影时,它会更难,因为制作电影很难,比和一群朋友聚在一起排一部戏剧更难。因为你需要准备伙食、设备,你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我认为潘佩罗的思维方式与剧团非常接近。例如,作为导演,我们每个人都会操作摄影机。我们都会操作录音机。我们都会使用设备。所以,如果我们找不到人来做这些事,我们可以自己做。所以在这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不需要像专业人士那样做事。 要知道,《迷雾中的她》中我怀孕时的所有镜头,都是我丈夫拍摄的。他不是摄影师,他是制片人,也是电影里的演员。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准备,以便在外出拍摄时能够拥有完全的自主权。我们为此做好了准备,即使我们得放弃技术团队,我们也可以这样做,然后出去拍摄。我认为我们从戏剧中学到的是,在剧团里,一名演员的基础培养,是和他们的表演生活同时进行的。他们作为演员相互理解,一起工作,一起排练。而在电影中,电影通常是在一个非常固定的时段制作的,比如说一年中的六周。但我们一直在拍摄,所以我们设法使我们作为影人的培养也保持恒定。不仅是在生活中那些孤立的时刻拍摄,而是让拍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训练形式,为了学习制作电影。我认为这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更复杂的表达形式,尤其是当一部电影需要在六个月内制作完成时。所以电影的复杂性更高。
异见者:这种长期日常训练的思维很有启发性。潘佩罗目前正在做什么,能同我们分享一些吗?
LC:我不确定。不,因为我们正在做…… 我正在写一部将在阿根廷和意大利之间拍摄的电影,但我还处于这个过程的开始阶段。我们正在完成阿列霍·莫吉兰斯基的一部新片,我们试图在二月份完成剪辑,这样我们就能了解什么对电影最有利,我们是否要参加电影节,是要尝试在七月之前还是七月之后参加电影节,取决于日程安排。然后,我们有三部大项目:分别由马里亚诺、阿列霍和我执导,我们必须了解如何在不改变工作方式的情况下转向更大规模的结构。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制作这些更有野心的电影。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如今做这些电影的时间更少,精力更少,所以我们不能花十年时间拍摄一部片子,像《花》那样,或者像《迷雾中的她》花费六年时间。我们必须找到其他方式,以便与我们生活的当下保持同步。但这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所以很难给你一个答案。我的意思是,我们有手里有很多作品,只是我不知道我们首先要做什么,要怎么做。这是个谜。
异见者:潘佩罗是否会拍剧集或者更商业的电影?
LC:我仍然不认为我们需要去拍商业电影。我仍然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尝试,玩弄形状和形式。我认为在商业电影领域,这可能不被允许。所以我不是说我们永远不会拍商业电影,也许我们会。但我不确定现在是这样做的时机,因为我们仍在努力寻找和发明新的东西。而且我认为,这个行业对有想法的导演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你知道,现在一切都很标准化。所以我不确定我们现在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仍然觉得我们必须去发现事物,去发明,去拍我们想拍的电影,并不去被老板们支配,不是吗?
异见者:我们一直很欣赏的一件事是,潘佩罗依旧在用拍摄《花》的那部佳能单反相机,甚至还有拍摄《非凡的故事》时的录像带相机。用于拍摄的机器似乎从未改变。尤其是在奥古斯丁这里,马里亚诺曾说他和这台机器已经产生了极强的默契。在如今科技迭代十分迅速的情况下,这种与一台旧摄影机之间的陪伴,某种程度上就是你们的电影。
LC:太客气了。

为 Opening Doors from Inside: a conversation with Laura Citarella on El Pampero Cine – LA FRÉDÉRIQUE – journal of cinema.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