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手册》& 让-克洛德·比埃特 X 让-马里·斯特劳布 & 达尼埃尔·于伊耶
这篇采访的法语原文最初发表于《电影手册》1995年“电影音乐”专刊中。采访者为Thierry Jousse、Vincent Vatrican以及让-克洛德·比埃特和Dominik Loss。我翻译所用的英文版文字出版于2016年在Sequence Press发行的斯特劳布-于伊耶生平文字选集《Writing》中,该版本且仅选用了和《安娜·玛格达丽娜·巴赫编年史》有关的部分内容。我在翻译稿最后附上了书中的英文注释部分。
Interview on Chronicle of Anna Magdalena Bach
《电影手册》(Cahiers):您一直说“巴赫电影”(Bach film)是您的第一个项目。为何选择巴赫?
让-马里·斯特劳布(JMS):源自生活所见。我以前的朋友弗朗索瓦·路易(François Louis)是钢琴和管风琴演奏家,因为他我发现了巴赫。也要感谢《乡村牧师日记》。但这都不是选择巴赫的真正答案。
达尼埃尔·于伊耶(DH):在当时,你告诉我你发现有很多完全不拥有长久音乐背景的人,他们可能听海顿或者莫扎特会睡着,但听巴赫他们不会。

JMS:因为作品是如此的浓密,如此辩证地、紧密地组织起来,因此我觉得在银幕上,它会拒绝被文本化。
Cahiers:但《编年史》的想法也是来源于一个文本?
DH:从来就没有任何文本。安娜·玛格达里娜从来不写日记,也不记述;她什么也没有写。我们拥有的唯一属于她笔下的,是一本《圣经》里的铭文。
JMS:除此之外,她也有抄写乐谱。唯一可考究的出自于她的文献,是她给自己堂兄弟的信,但这些都已经遗失了。还有一些在巴赫死后口述给抄写员的信件,是为了向莱比锡镇议会讨钱。当然还有Esther Meynell的小说《安娜·玛格达丽娜·巴赫的小编年史》,于1933年发行于伦敦。
DH:但那时她并没有提及(安娜·玛格达丽娜的)名字。但当时由于音乐理论家的抗议,这个“编年史”才在标题上加上她的名字重新印刷。但正如伏尔泰曾说的:“谎言…”
JMS:“…一旦被广为流传,便成为了真相。” 1
Cahiers:但即便这样,还是有文本。
JMS:只不过我们没从那本小说中引用哪怕一个字。我们建构出了一个文本来讲这个故事:一些取自克滕(Köthen)宫廷的账目登记册,一些取自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Carl Philipp Emanuel Bach)所写的“讣告集”,以及最重要的,一些巴赫本人的信件,其中他会写“我”,她会说“他”、“斯巴斯蒂安”。但我们创作的这个编年史是完全虚构的。我想我们首先想要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其次,因为巴赫在音乐工作本身的文本上又比许茨(Schütz)更进了一步,而那些文字的力量是我们可以去提取的。在当时,我曾经会胡扯一些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说的话:“音乐什么都无法表达”,因为对于巴赫这恰恰相反。他不仅能表达情感,他还能传递气,传递火……
DH:和风。选择巴赫还有另外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我们对于当时人们拍摄音乐的手法而感到厌恶。除了马克斯兄弟的作品或者《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 2)。另一个原因则是我们已经厌烦了当时对巴赫的演绎,那些十九世纪式的演奏——那些大型管弦乐团,那些两百人的合唱组来演奏《马太受难曲》(The Passion According to Saint Matthew)等等,跟他音乐的本质完全无关。而事实上,巴赫手下只有两组十二人的男孩——三个高音部、三个中音部、三个次中音、三个低音,而且当时在莱比锡(Leipzig)没有女歌手——被路德教派的统治者禁止。3
JMS:相比于克滕,由于那里主要是加尔文主义者,且女性有权利进入管风琴室。他在写那些音乐的时候就非常明确地考虑了演奏方式,并没有做自己能拥有两百人的管弦乐团和合唱团的白日梦。
DH:然后是最后的推动,我们的朋友给我们带了一张唱片来给我们听。我们一听就跟对方说:“我们就要他了!” 他就是古斯塔夫·莱昂哈特(Gustav Leonhardt)。
JMS:莱昂哈特当时只发行了两张唱片,一张是在美国发行的大键琴演奏《赋格的艺术》(The Art of the Fugue),一张在维也纳和Alfred Deller合作的两部清唱剧。我们当时知道他住在阿姆斯特丹,就坐了火车去看他。他告诉我们他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一下。那是在一个冬天,我们在泰瑟尔岛上住了几天,而在我们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会拍这部电影。” 那时是1957年。
Cahiers:在当时,几乎完全没有用年代乐器演奏的录音版本。
DH:在当时什么也没有。当时在科伦有一支音乐训练队叫Cappella Coloniensis,它的经理是Eduard Gröninger。他拒绝让我们使用他的乐团,因为他觉得乐团穿着年代的服装会很搞笑。
JMS:August Wenzinger,Schola Cantorum Basiliensis(译注:位于瑞士的一所专注早期音乐演奏的学院)协奏曲团的队长(他手下包含了Cappella Coloniensis三分之二的乐手)想要帮助我们拍摄这部电影,告诉我们:“我们决定要绕过那个人。” 我们需要两组乐手:一组科滕宫廷的乐手,和一组莱比锡教堂内的乐手。在当时,尼古劳斯·哈农库特(Nikolaus Harnoncourt,奥地利指挥家)有一支小型乐队,足以演奏影片开始时的《勃兰登堡协奏曲》(Brandenburg Concerto)片段。他本人扮演了安哈尔特-克滕(Anhalt-Köthen)的王子。
让-克洛德·比埃特(JCB 4):由年代乐器演奏的音乐当时已经作为一些保留剧目出现。比如说,在布鲁塞尔有这样演奏中世纪音乐的乐团。
JMS:你不该夸大我们的价值!
DH:不过并没有人以那种方式演奏清唱剧以及指导男童合唱团。
Cahiers:(问JCB)您是什么时候最早看到这部电影的?
JCB:我当时从罗马前往慕尼黑去看这部电影。我们躲在积雪似的毛毯下过境慕尼黑;我们在一家面包店停下买了三明治,然后前往剪辑室,一卷一卷地在剪接台上看完了电影。
JMS:你一定是唯一一个像莱昂哈特这样生更半夜赶过来,在剪接台上看了片子的人。
DH:然后莱昂哈特惊叫到:“巴赫倒放起来像施特劳斯!”
JCB: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从第一到第二卷那里的一个片段,管风琴三重奏奏鸣曲搭配风景版画的影像。
JMS:为什么?
JCB: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与音乐的关系。
JMS:你指的是,当莱昂哈特在演奏管风琴时?
JCB:当然。但那显然也是因为乐器的音调。
JMS:那是吕讷堡的圣约翰教堂的管风琴。这一段是后退一步,去展开巴赫的童年;在德国的北方,那里的管风琴或许要比Silbermann——巴赫的朋友制造的要更美妙。
Cahiers:当时影片的反响如何?
DH:电影在1968年的柏林电影节上放了,动荡的一年。我们拒绝在那里出席,因为当时警察活动非常多。似乎当时在那有某种剧院内的冲突,有人喊道:“Bach war doch kein Hampelmann”,意思是“巴赫不是木偶。”
JCB:那是因为你用前所未见的方式展示了巴赫。
DH:不完全是。人们意识到在巴赫之上还有统治者,而且发现他也谱写了功能性的音乐。当时对于十九世纪的概念是艺术高于一切。像卡拉扬(Karajan)这样的人鼓吹了这样的想法。5
Cahiers:您的概念是要远离“受启发的天才”那种刻板印象。您是否有看过阿贝尔·冈斯(Abel Gance)的《贝多芬传》(Un grand amour de Beethoven, 1937)?
JMS:我们在墨西拿路(rue de Messine)看的。我们很喜欢这部电影,但是…
DH:… 对于巴赫电影的首要概念是它需要音乐演奏家而不是演员。如果不是这个需求,我们在更早之前就能把它拍完。
JMS:那样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在十年前就跟库尔德·于尔根斯(Curd Jürgens 6)拍了!我们可以这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仅是想要拍音乐自身,而是演奏一首音乐这件事的整个执行过程,然后甚至能去做一个把一整套作品聚拢起来的整理性工作,在这里指的就是巴赫的作品。其次,再将传记、编年史也聚拢到一起,甚至能够包括进巴赫的人格。有些东西存在于这个焦点上,并且以此而制作出来,就像布莱希特(Brecht)对爱的定义一样,是“做一件事情,但以所有他者的容量来做。” 换句话说,是莱昂哈特与那些乐手在执导巴赫,以此,以这个规模,来更加透明更加清晰地去诠释音乐。除此以外,莱昂哈特在当时还没有指挥过一个乐团。后来很久以后才看到电影的米夏埃尔·吉伦(Michael Gielen,奥地利指挥家)说,莱昂哈特指挥的方式非同寻常。
DH:我们有巴赫想要的(乐手和歌手)人数,因为他曾经写过一个宣言,我们在片子里也有引用。我们非常了解他具体想要的人数,但他也抱怨没有候补:如果一个歌手生病,那就砸了。
Cahiers:您是否有拍很多条?
JMS:这要看是哪些片段。
DH:《马太受难曲》我们用的是第八条,我记得。
JMS: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完整的,因为会出错,或者莱昂哈特自己叫停了他们。
DH:而有意思的是,这第八条中,上升部并不完美;没有组织好。
JMS:Louis Hochet,我们的收音师在那用他的Nagra牌录音机录制,他还觉得我们会叫停拍摄。
DH:没人说一句话,而最终这一条是最好的。然后我们加上了旁白,因此旁白的最后一个词遮盖了上升部。这在音乐里经常发生:有的一开始的错误在后面制造出了灵光。
Cahiers:您是否能判定或者评价每一条的好坏?
JMS:一点点。我们不是音乐家,但毕竟我们“有眼睛和耳朵”,就像卡夫卡会说的那样。而达尼埃尔拷贝了不少各种各样的乐谱来准备我们在电影中听到的演奏,一一匹配巴赫当时的形式。
DH:我因此很自豪,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如何读乐谱,为了这部电影专门学的。
JMS:你当时已经很开心能够辨别《音乐的奉献》(The Musical Offering)里的音符,但那是拍这部电影很久之前了。
DH:那也是为了准备这部电影!
Cahiers:(问JCB)您当时是否已经对年代乐器产生兴趣?看到电影时您有惊讶吗?
JCB:没有,我有准备过,因为当时已经看了和《没有和解》(Not Reconciled)相关的采访,其中就有预告《巴赫》的前期制作,我立马就对这个诠释巴赫的方向产生了兴趣;我觉得那都很自然。
JMS:我觉得很好的一点是,如果拍《巴赫》时我们得到了批准去博物馆里用那些原生的乐器,掸一掸尘土,那估计就会是一部糟糕的电影。更别说并不是所有的乐器都是斯特拉迪瓦里级别的。在Cappella Coloniensis,有一些年代乐器的复制品,和一些Skowroneck制造的大键琴。但那些都是能用的乐器。这些都让我想到了《所有世界的早晨》(Tous les matins du monde, 1991)。阿兰·科诺说他收到了《编年史》和《莫扎特传》(Amadeus 7)的影响,但他一定也在别的地方寻找过灵感,毕竟是不可能把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的。
DH:他说他看了电影不知道有多少次,但就像格林纳威那样,他完全没意识到我们一支蜡烛都没有点,而是有许多各种各样的窗户!
JMS:在那方面我们也是花了很多心思。蜡烛对于茂瑙的电影很好,但我们并不是在效仿茂瑙。尽管很多上述的东西,这部电影在某种感觉上依旧是现代的。
JCB:于是就有了那歪曲的火把。
JMS:当地的记述说:“学生们聚集在一个点了六百支火把的小镇广场上”,于是我们就用一支火把来照明乐谱。那里用了背投技术,帕索里尼(Pasolini)对此很震惊,但他其实也有绘画的背景,因为在那里,16世纪镇议会大楼的仰视景深镜头和俯拍的大键琴前演奏的领唱者(他在第一个镜头里演奏数字低音以及指挥)之间产生了一个冲突。这个构图反应的是那唯一一个能让王子能在房子高处能看到演奏现场的角度,毕竟(唱词中)有“赞美你的好运,萨克森,因为上帝接受了国王的宝座。(Take your Happiness, blessed Saxony, because God supports the throne of your king.)” 电影也有点是关于巴赫与上帝之间的关系。Günter Peter Straschek——在《阿诺德·勋伯格电影配乐介绍》(Introduction to Arnold Schoenberg’s “Accompaniment to a Cinematographic Scene”)中能看到他,曾经在法兰克福大学的课堂上对那些对着“上帝”二字哄笑的学生说:“如果你在听到’上帝’二字时就在开始发笑,你永远都不会制造出一场革命。” 这也是电影的一部分。那句话是一句俗语的早期版本,后来几年后便出现在了上述的《B小调弥撒》(Mass in B minor)中和那撒的部分。整部电影的结构遵照巴赫演奏宫廷音乐会、之后的清唱剧、大键琴以及管风琴的各个对应年代。这些重组制造出了各个演奏片段模块,反映了一个编年史,而这些模块也不以陈旧的方式连接在一起。这是莱昂哈特在芝加哥首次看到电影时发现的。他是去听声音的响度是否在没有在过度饱和的情况下恰到好处。他坐在剧院的最后一排,担心了一小会儿,最后给我们寄了一张明信片,说:“我从未听到过这么好的音响效果。这是光学发声,而我以为是像在混音时听到的磁录式声音。第一次能安稳地看这部电影,我对影片的展开过程印象非常深刻。” 尽管每个镜头都被分开反复读解观察,莱昂哈特发现了建构的过程,这也算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崇高的嘉奖。
Cahiers:(对JCB)您对影片印象深刻的点在哪?
JCB:主要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影片时长上的变化。用三重奏奏鸣曲配合那些版画里的风景对我而言像是对影片速度的调整,而就是在那时你能瞬间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不仅是镜头时间,而是年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情感。况且,在当时我还不知道那些三重奏奏鸣曲,而我永远忘记不了第一次在剪辑室看到这个奏鸣曲乐章时的时刻。
JMS:这是它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被演奏。弗朗索瓦·路易有一天跟我说:“你知道三重奏奏鸣曲吗?” 我说没有。“啊,斯特劳布!你必须立刻听听,你会喜欢的,有点像是游乐场音乐!”
Cahiers:您是否读过《Trafic》杂志第十五期里让-克洛德·比埃特关于立体声的起源的文章?8
JMS:1959年在慕尼黑,达尼埃尔的母亲给我们买了一套扩音器和唱片机作为结婚礼物。但我们只想要一个单体喇叭。卖家当时就想给我们两个一套的。我们不想要立体声出现在我们的电影里。这是一点让我们跟戈达尔很不一样的地方。在当时我们甚至比他更疯狂。从那第一次跟Wenzinger、莱昂哈特和Hochet(我们的老搭档)见面的时候,我们就讲明白了一个基本准则:一场演奏只用一支话筒。我们可以在《马太》一开始的合唱部时用三支,但不会是四支。
DH:而在当时,收音师会在每个座位底下放一个话筒。
JMS:但并不是为了录制唱片。
JMS:听着,就算哈农库特都跟我们说:“长舒一口气!” 他曾给德律风根(Telefunken)录制过巴赫的交响组曲,我已经不记得我们当时给了他多少支话筒。不过,那个录音师也不是个白痴。
JCB:但那已经是立体声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用这么多话筒。
JMS:立体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JCB:在唱片业,立体声从1955年开始被应用,一年之后立体声唱片就开始在市场上发行了。
JMS:电影用立体声太荒唐了。每当杜比这个词出现,我就开始亮红灯。首先,我不喜欢垄断,其次,每次我们带着自己的电影去电影院,我们都要要求他们关掉杜比,忘记这么做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因为声音会变得很空洞。它应该像一座管风琴一样,一年要调两次音,然而不会有人这么做。我记得有次在蓬皮杜中心看让-吕克的那部关于德国的电影(指《德国玖零》,Germany Year 90 Nine Zero),他被告知说声音有点刺耳,然后他跟我们说:“在任何情况下声音都不应该刺耳;声音肯定是被调错了。” 当然,一般四次里有三次都是调错的。
JCB:您知道在希腊语里“Stereo”是什么含义吗?被剥夺,被分离。
JMS:从哪里?生活吗?
JCB:也许。
JMS:从空间?
JCB:大概是的。
JMS:自然地,真实时间被强加在我们上面,因此真实空间也阻挠我们。不然,你会发现不再是真实时间了。我们跟Paul Schöler做《编年史》的混音。他跟我们说:“我觉得一个喇叭应该被放在银幕后面,银幕上会布满小洞让声音传过来。这才是我们混音的方式——声音来源于影像。” 当你要混杂起文字、评论、音乐和杂音时,你必须要更加小心工作。这也是我们跟Louis Hochet就我们的下一部电影中提前混录的交响部分而谈好的准则——如果在他那里用立体声的效果好的话,那对于我们而言用单声道也会好,反之亦然。
DH:但尤其严重的问题在于扩音变得越来越夸张,已经开始对音乐演奏本身产生影响。
JMS:戈达尔跟我们一样懂这个;我曾听到他跟Manfred Blank说:“技术创新与艺术倒退永远肩并肩,以至于它们不再有任何意义。” 这句话应该成为常识。
JCB:杜比强迫音乐家们以更高的响度来演奏。这不是为了在真实空间里听到音乐。它必须变得像通风的,抽象的。更何况,音乐家们都希望在录制中听到一些混响,去听到有“空间感”的声音。
DH:而这和巴洛克式的音乐背道而驰。
JMS:从一开始,哈农库特就警告我们说:“巴洛克式音乐是一种必须在被大理石包裹的听觉空间下被听到的音乐。”
JCB:或者最起码在木质的环境中。
JMS:他倾向于大理石,因为他不想要回响的效果。
DH:在当时还没有立体声的Nagra牌设备,所以我们就用单轨来录制,Hochet在录制时要小心,因为没有补救机会。
JMS:莱昂哈特最大的担忧在于平衡。他知道他想要如何录制。要平衡合唱团和管弦乐团。在巴洛克式音乐中,这种平衡比任何别的种类音乐都更需要做到完美。Hochet从来没有录制过音乐,除了为百代(直接用精确声音)。然后,在拍摄进行了几天后,莱昂哈特与他握手说道:“祝贺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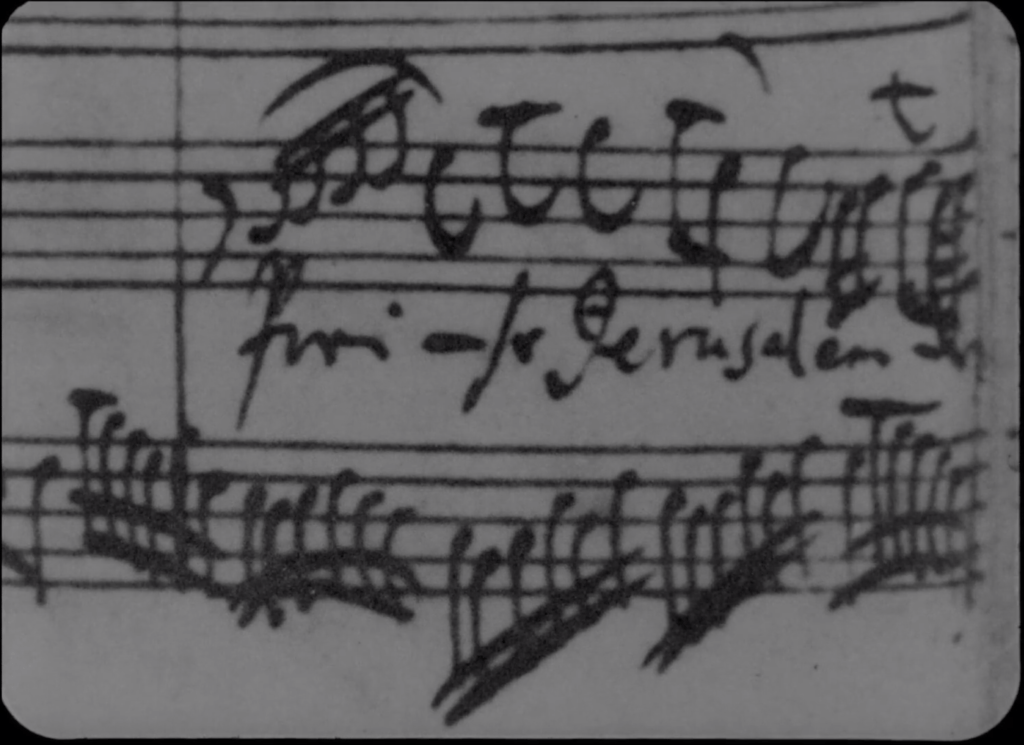
原文译注
1995
Original language: French
First published in Cahiers du cinéma, special issue, “Musiques au cinéma,” hors série (1995): Interview with Thierry Jousse and Vincent Vatrican with Jean-Claude Biette and Dominik Loss. We reproduce here only the excerpts on Chronicle of Anna Magdalena Bach that was republished in Danièle Huillet and Jean-Marie Straub, Chronique d’Anna-Magdalena Bach (Toulouse: Éditions Ombres, 1996), 129-140 (text reviewed and corrected by DH in November 1995).
NOTES
1 The dictum (“Mentez, mentez, il en restera toujours quelque chose.”) is commonly attributed to Voltaire. Its real author may, however, be his contemporary, the French playwright Pierre Beaumarchais who has Don Bazile say in The Barber of Seville: “Calomniez, calomniez, il en restera toujours quelques chose.”This quote was subsequently also attributed to Vladimir Lenin.-Ed., this and all subsequent notes.
2 Howard Hawks’ film adaptation (1953) of the 1949 stage musical.
3 Although Martin Luther encouraged his ministers to marry and even insisted on it, he did not envisage a wider role for women in his reformed church.
4 Filmmaker Jean-Claude Biette (1942–2003) began his career writing for Cahiers du cinéma in the 1960s and early 1970s. In 1991, he co-founded with Serge Daney the review Trafic.
5 Herbert von Karajan (1908-1989): Austrian conductor who conducte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for thirty-five years and who was one of the top-selling classical music artist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6 Popular Austrian-German actor known in Hollywood as Curt Jürgens (1915–1982).
7 Milos Forman’s 1984 film about Mozart.
8 Jean-Claude Biette, “Les Enfants de Godard et de Pasiphaé,” Trafic: revue de cinéma, no. 15 (Summer 1995): 118-130.

为 关于声音、物质性和虚构的几点思考 – LA FRÉDÉRIQUE – journal of cinema.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